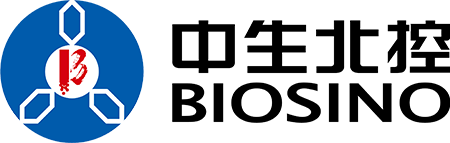β-HBβ -羟丁酸测定试剂盒(β-羟丁酸脱氢酶法)
--糖尿病患者酮症或应急状态的监测指标
样本类型:新鲜无溶血血清
适用仪器:本试剂盒适用于绝大多数主流生化分析仪
试剂盒优势
1.采用酶法测定,提高抗干扰能力
2.线性范围宽,0.01~4.50mmol/L
指标简介
β-羟丁酸(β-hydroxybutyrate,β-HB)、乙酰乙酸和丙酮总称为酮体(ketone bodies),其中β-羟丁酸约占78%。酮体主要来源于游离脂肪酸在肝脏的氧化代谢产物[1]。同葡萄糖一样,酮体可穿过血脑屏障被大脑利用,在葡萄糖缺乏时可代替葡萄糖为机体供能,是人体在饥饿状态下的重要能量来源。体内酮体含量反映了机体代谢和酸碱平衡的状态[2]。正常人血液中酮体含量极少,当某种生理状态(如饥俄、禁食、严重的妊娠反应)导致体内糖供-酸就成为主要供能物质,可在肝脏内大量氧化生成大量酮体。酮体在肝内生成后经血液转运至肝外组织(如心、脑、肌肉)利用,而肝细胞因缺乏相关的酶其自身不能利用酮体[2]。当肝内酮体生成的量超过肝外组织的利用能力,血酮体浓度就会过高,导致酮血症和酮尿症。乙酰乙酸和β-羟丁酸都是酸性物质,在体内大量堆积时会引起酸中毒。妊娠期妇女可因为严重的妊娠反应产生酮症。糖尿病酮症(diabetic ketosis,DK)和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iabetic ketoacidosis,DKA)是较为常见的病理性酮症状态,其基本环节是胰岛素缺乏或有效作用减弱,同时多种反向调节激素,如胰升糖素、儿茶酚胺、肾上腺皮质激素及生长激素等水平升高[2]。更多时候,血酮检测的是β-羟丁酸,而尿酮检测的乙酰乙酸及丙酮[3]。尿酮与血酮有一定相关性,但并不呈线性关系:尿酮+相当于血β-羟丁酸浓度0.5 mmol/L,尿酮++相当于0.7 mmol/L,尿酮+相当于3 mmol/L。研究显示,治疗开始的时候血酮与尿酮无相关性,平均治疗7.8 h 血酮和尿酮才有相关性。如无特殊说明,本文所述血酮特指血β-羟丁酸。血清中β-羟丁酸的测定方法包括酸氧化比色法、气相色谱法、酶法和毛细管电泳法等。其中,酶法灵敏度高、速度快且样品用量少,可直接测定,适用于自动化分析仪,目前为β-羟丁酸测定的优选方法[1]。D3羟丁酸与β-羟丁酸两者实为同一物质,D3羟丁酸是β-羟丁酸的立体化学命名形式,实际无化学结构差异。在医学检测中,"β-羟丁酸"为通用名称,涵盖所有立体异构体(主要为D型)。
检测原理
在氧化型辅酶Ⅰ(NAD+)存在时,β-羟丁酸在β-羟丁酸脱氢酶(β-HBDH)的催化下,生成乙酰乙酸(AcAc)和还原型辅酶Ⅰ(NADH);在黄递酶的催化下,NADH与氧化型碘硝基氯化四氮唑(INT)发生氧化还原反应生成氧化型辅酶Ⅰ(NAD+)和还原型INT,还原型INT在505nm处有吸收峰。用生化分析仪在波长505nm(480~520nm)处,检测还原型INT颜色的变化,可计算出血清中β-羟丁酸的浓度。
临床应用
- 血清β-羟丁酸(β-HB)升高见于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及各种原因所致的长期饥饿、饮食中缺少糖类或营养不良等。β-HB测定是评估酮症及其相关疾病的关键工具,尤其在糖尿病急症、代谢性酸中毒鉴别及特殊生理/病理状态中不可或缺。
- 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的诊断、严重程度判断、监测及疗效评估:DKA是糖尿病患者最常见的严重急性并发症,也是40岁以下1型糖尿病死亡的最主要原因[4]。DKA是由于胰岛素不足和升糖激素不适当升高引起的糖、脂肪和蛋白质代谢严重紊乱综合征,临床以高血糖、高血酮(血β-羟丁酸升高)和代谢性酸中毒为主要特征。约10%的 DKA 患者表现为血糖正常的糖尿病酮症酸中毒(euDKA)[5]。
- β-羟丁酸可用于辅助糖尿病的诊断与分型诊断,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血β-羟丁酸升高,≥3 mmol/L)是1型糖尿病(T1DM)的常见典型特征,而2型糖尿病(T2DM)虽亦可发生,但相对少见[5]。
- β-羟丁酸是DKA的核心诊断标志物,其浓度≥1 mmol/L即为高酮血症或称糖尿病酮症(DK),其浓度≥3 mmol/L可提示DKA,且动态监测有助于评估胰岛素治疗反应和病情改善[6]。
- DKA的严重程度根据血糖水平、血β-羟丁酸水平、动脉血pH值、血碳酸氢根水平和意识状态改变程度分为轻度、中度或重度。其中轻度、中度DKA的血β-羟丁酸水平为3.0~6.0mmol/L,而重度DKA时血β-羟丁酸水平>6.0mmol/L [5]。
- 在严重酸中毒患者,β-羟丁酸与乙酰乙酸的比值可从正常人的2:1升高到16:1,在酮症酸中毒的早期阶段,比值可达最高点,而继续治疗,该比值将随着β-羟丁酸被氧化成乙酰乙酸而降低。因此,通过跟踪监测β-羟丁酸可更真实地反映酮症酸中毒的状况[1]。
- 新诊断T2DM患者胰岛素的起始治疗参考指标。新诊断T2DM患者如有明显的高血糖症状、酮症或DKA(β-羟丁酸≥3 mmol/L),优选胰岛素治疗。待血糖得到良好控制和症状得到显著改善后,再根据病情确定后续的治疗方案[5]。
- 监测血酮值可评估DK及DKA治疗的有效性。血酮下降表明DKA的缓解,血酮下降速度可作为疗效的评估指标。
- 在美国,血酮检测(即血β-羟丁酸)是患者院外糖尿病管理的重要手段。一项调查显示,与尿酮检测相比,院外患者更容易接受血酮检测,并通过积极有效的检测显著降低了酮症入院、急诊次数。从卫生经济学角度,及时院外血酮监测是一种节省医疗成本的选择[3]。
- 血酮水平还有一定的预测预后价值。患者住院天数与血酮相关但与尿酮不相关;血酮仪测得的血酮每增加1 mmol/L,死亡率增加24%;生化仪测得的血酮每增加1 mmol/L,死亡率增加93%;尿酮水平每增加1 mmol/L,死亡率增加5 % [3]。
- 糖尿病患者胰岛素治疗不当、血糖控制不佳(随机血糖≥13.0 mmol/L)、重症感染、严重应激,儿童和老年糖尿病患者,服用药物(如糖皮质激素、苯乙双胍等)、妊娠期、某些内分泌疾病(如库欣病、肢端肥大症及胰升糖素瘤等)、长期饥饿出现低血糖时、口服或静脉输入大量葡萄糖后,有发生酮症的潜在危险,应及时进行血酮体的检测,可有效地预防或减少DKA的发病率和死亡率[3]。
- 高渗性高血糖状态的辅助诊断:高渗性高血糖状态(HHS)是糖尿病的严重急性并发症之一,临床上以严重高血糖而无明显DKA(血β-羟丁酸<3.0 mmol/L或尿酮小于++)、血浆渗透压显著升高、脱水和意识障碍为特征[5]。
- 非糖尿病性酮症的鉴别诊断:β-羟丁酸水平可区分不同病因的酮症。酒精性酮症酸中毒:乙醇代谢导致NADH/NAD⁺比值升高,β-羟丁酸显著升高(常>5 mmol/L),常伴随β-羟丁酸和乙酰乙酸同步升高[7]。生理性酮症(如生酮饮食):β-羟丁酸升高幅度较小(1-3 mmol/L),且无酸中毒[8]。
- 生酮饮食( KD) 是一种以脂肪及脂肪酸为主要构成的配方饮食,含高比例脂肪、适量蛋白质和低碳水化合物,最早由Wilder于1921年报道,作为难治性癫痫的一种补充疗法。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KD不断被应用于其他疾病的辅助治疗,其安全性、有效性得到了进一步的探索和研究[9]。定期监测血β-羟丁酸水平有利于维持癫痫儿童的正确生酮饮食。
- 饥饿性酮症:轻度β-羟丁酸升高(通常<3 mmol/L),且无代谢性酸中毒。王蕤等[10]研究发现,妊娠期糖尿病(GDM)患者的酮症主要为饥饿性酮症。
- 小儿饥饿性酮症多数是由于小儿腹泻导致腹泻过度,机体丢失大量碱性物质,进食少,热卡不足,同时由于肠吸收不良,机体得不到正常能量供应,小儿的代偿能力较差,导致体内脂肪分解增加,肝脏脂肪酸代谢相对旺盛,产生大量酮体。β-羟丁酸对小儿饥饿性酮症的诊断有重要意义[11]。
- 血β-羟丁酸检测可作为糖尿病昏迷的诊断及鉴别诊断指标。部分患者在酮症酸中毒和昏迷前可由于糖尿病未被诊断而无病史,因此对原因不明的昏迷、失水、休克的病者,均应考虑检测β-羟丁酸,判断是否酮症酸中毒的可能性。酮症酸中毒亦可见于饥饿和酗酒的病者,多由于胰岛素过量而导致的低血糖昏迷时,β-羟丁酸水平升高,而神经性低血糖昏迷时,β-羟丁酸水平正常。根据病史、β-羟丁酸不高甚至低于正常,可鉴别酮症酸中毒低血糖昏迷和神经性低血糖昏迷。对于有糖尿病史的急诊病人以及不明原因的昏迷、失水、休克患者进行β-羟丁酸的监测,便于正确有效的治疗[12]。
- 生酮饮食及神经代谢疾病管理:β-羟丁酸监测可评估生酮饮食依从性(目标浓度0.5-3 mmol/L),并用于癫痫治疗的代谢调控。研究证实,β-羟丁酸可作为脑缺血损伤的替代能源,改善神经元代谢[8]。生酮饮食通过升高β-羟丁酸抑制癫痫发作,其浓度需维持在特定阈值以保障疗效[13]。
- 代谢性酸中毒的病因鉴别:β-羟丁酸升高提示酮症性酸中毒,而乳酸酸中毒(如休克)或肾小管酸中毒时β-羟丁酸水平正常,有助于快速区分酸中毒类型。
- 低血糖(如神经性低血糖、β-胰岛素瘤)的诊断与鉴别诊断:胰岛素瘤患者因肿瘤持续分泌胰岛素,导致低血糖发作时胰岛素水平显著升高,抑制脂肪分解,血β-羟丁酸水平通常低于正常低血糖反应(如饥饿性低血糖)[14]。神经性低血糖(如反应性低血糖)发作时,因胰岛素分泌相对过多,脂肪分解受抑,β-HB水平通常正常或轻度升高,与胰岛素瘤的低β-HB形成对比[15]。胰岛素瘤患者低血糖时血β-羟丁酸水平显著低于外源性胰岛素过量或神经性低血糖,提示β-HB可作为鉴别指标。
- 糖原累积病(GSD)的诊断与鉴别诊断:糖原累积病Ⅰ型(GSDⅠ)患者因葡萄糖-6-磷酸酶缺乏,肝糖原无法分解为葡萄糖,导致空腹依赖脂肪分解供能。糖原累积病Ⅰ型患者空腹时β-HB水平显著升高(>3 mmol/L),是诊断的关键指标。β-HB升高可与其他低血糖病因(如胰岛素瘤)区分[16]。
- 遗传性代谢疾病的辅助诊断:有机酸血症(如丙酸血症):β-羟丁酸可能因代谢受阻而降低,需结合血氨、乳酸及基因检测。线粒体疾病:能量代谢障碍可导致酮体生成异常,β-羟丁酸波动提示线粒体功能异常。
- 慢性肾衰竭或脓毒症、休克等危重患者下的代谢评估:慢性肾衰竭:毒素蓄积可能影响酮体代谢,β-羟丁酸水平升高提示代谢应激。脓毒症、休克等危重患者中,β-羟丁酸升高可能反映胰岛素抵抗或组织缺氧导致的脂解加速。其水平与病死率相关,β-羟丁酸>3 mmol/L的危重患者住院病死率显著增加。
- 特殊人群的代谢监测:妊娠期糖尿病:妊娠剧吐(严重呕吐)或胰岛素抵抗可能诱发酮症,β-羟丁酸测定有助于及时干预。患糖尿病或妊娠糖尿病妇女在怀孕期间血糖控制不良,血β-羟丁酸水平升高,导致胎儿宫内慢性缺氧,促红细胞生成素水平升高,影响胎儿红细胞发育。Gonzalez A等回顾性分析发现,定期监测并控制母体β-HB水平可降低胎儿红细胞增多症发生率。美国糖尿病协会(ADA)指南建议对GDM孕妇定期监测血糖(FPG/HbA1c)及酮体(βHB),以预防胎儿高胰岛素血症及红细胞增多症[17]。新生儿筛查:新生儿暂时性高胰岛素血症或先天性代谢缺陷(如糖原累积症)常伴酮症,β-羟丁酸检测可辅助鉴别低血糖病因。例如,β-羟丁酸与胰岛素水平反向变化,有助于诊断高胰岛素性低血糖症。新生儿酮症相关遗传性疾病的筛查中,β-羟丁酸也被建议纳入常规检测指标。
- 检查人体酸碱平衡除检查电解质分析之外,还应检查血清β-羟丁酸,监测病情加重及缓解情况[18]。
适用科室
|
适用科室 |
适检人群 |
|
内分泌科 |
1型糖尿病(T1DM), 2型糖尿病(T2DM)(血糖控制不佳或出现酮症),妊娠期糖尿病(GDM),糖原累积病(GSD),其他代谢性急症(如DKA、HHS) |
|
急诊科 |
急性昏迷/休克(原因不明),严重感染或创伤,酗酒或药物过量(如苯乙双胍),急性低血糖昏迷 |
|
重症医学科(ICU) |
脓毒症/休克患者,多器官衰竭患者,危重患者(如心源性休克、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 |
|
儿科 |
新生儿低血糖(尤其暂时性高胰岛素血症),儿童糖尿病(DKA管理),小儿腹泻相关饥饿性酮症,遗传性代谢疾病(如GSD、线粒体病) |
|
神经内科 |
癫痫患者(生酮饮食治疗),脑缺血/脑损伤患者 |
|
营养科 |
生酮饮食患者(癫痫、肥胖、代谢综合征),特殊饮食干预患者(如低碳水化合物饮食) |
|
妇产科 |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GDM),妊娠剧吐导致酮症孕妇 |
|
遗传代谢病科 |
糖原累积病(GSD),有机酸血症(如丙酸血症),线粒体疾病 |
|
感染科 |
严重感染(如败血症)合并代谢紊乱患者 |
|
新生儿科 |
新生儿低血糖症(尤其高胰岛素性低血糖),新生儿遗传代谢缺陷筛查 |
|
家庭/社区医疗 |
糖尿病患者(院外管理),长期饥饿或营养不良人群,生酮饮食依从性监测 |
参考文献
[1] 尚红, 王毓三, 申子瑜. 全国临床检验操作规程[M]. 第4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2] 尹一兵, 倪培华. 临床生物化学检验技术[M]. 第1版. 北京: 人民卫生出版社, 2015.
[3]中华医学会内分泌学分会. 中国糖尿病血酮监测专家共识[J]. 中华内分泌代谢杂志,2014,30(3):177-183.
[4]Wilson V. Diagnosis and treatment of diabetic ketoacidosis. Emerg Nurse. 2012 Nov;20(7):14-8; quiz 19.
[5]中华医学会糖尿病学分会. 中国糖尿病防治指南(2024版)[J]. 中华糖尿病杂志,2025,17(1):16-139.
[6]Kitabchi AE, Umpierrez GE, Miles JM, Fisher JN. Hyperglycemic crises in adult patients with diabetes. Diabetes Care. 2009 Jul;32(7):1335-43.
[7]Kraut JA, Mullins ME. Toxic Alcohols. N Engl J Med. 2018 Jan 18;378(3):270-280.
[8]Paoli A, Rubini A, Volek JS, Grimaldi KA. Beyond weight loss: a review of the therapeutic uses of very-low-carbohydrate (ketogenic) diets. Eur J Clin Nutr. 2013 Aug;67(8):789-96.
[9]孙蓉,吴群芳. 生酮饮食在各种疾病中的应用研究进展[J]. 内科,2018,13(6):878-882.
[10]王蕤,徐品颖,肖利. 妊娠期糖尿病患者发生酮症的临床特点[J]. 中华糖尿病杂志,2017,9(8):504-508.
[11]林列坤,潘昆贻,邓小燕. 血清β-羟丁酸测定在小儿饥饿性酮症诊断中的作用[J]. 检验医学与临床,2010,7(6):484-485.
[12]王冬环,赵月霞. D-3-羟丁酸检测与临床应用[J]. 临床和实验医学杂志,2006,5(2):142-143.
[13]Prins ML. Cerebral metabolic adaptation and ketone metabolism after brain injury. J Cereb Blood Flow Metab. 2008 Jan;28(1):1-16.
[14]Service FJ, O.B.P., Kao PC, et al., Hypoglycemia in insulinoma: clinical and diagnostic features. Am J Med. , 1981. 71(3): p. 379-384.
[15]Hussain K, A.-G.A., Hyperinsulinaemic hypoglycaemia: biochemical basis and management. Arch Dis Child., 2018. 103(7): p. 663-669.
[16]Chen YT, B.C., Lee MM, et al., Glycogen storage disease type I: diagnosis and management. . Curr Opin Pediatr., 2018. 30(4): p. 536-543.
[17]ElSayed NA, Aleppo G, Aroda VR, Bannuru RR, Brown FM, Bruemmer D, Collins BS, Hilliard ME, Isaacs D, Johnson EL, Kahan S, Khunti K, Leon J, Lyons SK, Perry ML, Prahalad P, Pratley RE, Seley JJ, Stanton RC, Gabbay RA, on behalf of the American Diabetes Association. 2. Classification and Diagnosis of Diabetes: Standards of Care in Diabetes-2023. Diabetes Care. 2023 Jan 1;46(Suppl 1):S19-S40.
[18]郑红,肖雪莲.β-羟丁酸的检测方法及临床应用研究[J].新医学导刊, 2008, 7(9):2.
指南共识